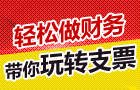我的快乐童年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已经年届不惑。不惑即豁然。那么豁然出什么道理来了呢?壮年的忙碌,青年的迷茫,少时的苦难,仔细比较,发现自己的童年是快乐的。我所指的童年是在14岁以前。
几乎每个人都回味着童年的无忧无虑的快乐。而我发现自己的童年更为快乐,一是相比于现在的孩子,应试教育这根指挥棒使得现在的孩子疲于奔命,他们几乎没有快乐可言。二是相对于那时其他的农村孩子,他们或多或少地要帮助大人做一些的劳动来挣工分,比如拔秧、分秧、割禾、拾穗、晒谷,而我的童年却是那么轻松。
上世纪的六十年代末,我出生在一个四面环水的赣江中的一个洲上,一个完全种旱地的农村。家乡以种茶为主,甘蔗也是主要作物。所以叫茶农,也叫蔗农。当然,因为是种旱地,几乎所有的经济作物都有,西瓜、芝麻、花生、棉花、萝卜、板栗、苎麻、油菜、红薯、大豆、车前籽、土豆、黎黍(高梁)、包黍(玉米)等,都种。也偶尔种麦。我父亲曾当过5队的队长,有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就有个老头来汇报情况,老头有点舌头硬,说话不清,反反复复几次才听明白:麦子、包黍(苗),全被鸡吃了。农户自己也有菜园、枣树、桔树、柚树、桃、李、梨等,野生的可换钱的还有蓖麻、籽树、半夏。记忆中好象也试种过旱稻,但因为不适宜,很快就没种了。对水稻的不熟悉,导致了我直到高中时还不明白为何每年学校会放两次农忙假,而每次师生们都要去割禾——不是割过禾了么,怎么还要去割?
因为是经济作物区,我们吃的是“返销粮”,即国家发给定量粮票,凭粮票到粮站买米,价格是每斤一毛八,而此时国家给我们茶叶的统购价是每斤三块多。那时我们家乡是有名的富裕村。在种粮区每个工分只有三四分钱的时候,我的家乡每个工分竟是一毛五。每到年底,几乎家家都能分到几百元钱。劳动力多的人家,甚至可以分到千元以上。生产队按人头分猪肉,每个人有两斤。
除了农业收入,家乡还办起了两个厂,一个是造船厂,年可造30吨以上木船两三艘。还有一个全电动化的制茶厂,杀青、捻条、烘干、成型,全机械化。我记得为建制茶厂,每家须交砖头几百块。为筹砖,不少人发明了探古墓法,用一个钢针探下去,听声音判断是古墓,还是只是一块石头。我还记得当时用船运来这些机械设备时,从没看过机械的我,是那么新奇。
因为要电动生产,就要有电力。用的是柴油发电机。既然有发电带动机械,何不用来照明?于是我们这个偏僻的洲上,成为全乡最早用电灯的村。
每天,造船厂的锯木声、打钉声、把桐油拌石灰再拌竹丝的膏嵌入船缝的声、制茶场的柴油发电声、制茶机的轰鸣声,响作一团,让对岸粮作区的人羡慕不已。岂止是对岸的人,十里八乡的人都羡慕,“嫁到洲上去”,成为许多姑娘的愿望。
茶叶能卖好价,自然质量要把住。除了制茶有工艺外,采茶也是个关键。胡乱地采,不仅降低茶叶质量,而且还采伤茶树,妨碍下季的发芽。采茶是手工活,也是作为孩子唯一能参与的体力劳动。为确保茶叶质量,生产队不许孩子帮忙采茶赚工分。这是我童年得以轻松的“德政惠策”,不知当时是谁当的大队长,他可是决定那时我们整整一代孩子童年生活的人。
采茶不用去,其他更重的农活也做不了。我们那时的孩子们啊,剩下的唯一的事就是玩耍。都玩些什么呢?
玩水。没事就跳进河里,一玩就忘记了时间,直到河水把手指都浸成皱纹,直到有点头晕了,才上岸。打水仗,扎猛子,看谁在水下憋得久,看谁能在水下游得远。那时的赣江水运繁忙,每见有船从下游开上来,我们就拼命游过去,扒上船,坐到船头大喊大叫,显示自己的能耐。有时大骂船员:“船上人,冇良心,打开竹门就骂死人”,是首儿歌。船员自然恼火,冲过来要打,我们则纵身一跳,走了。也扒上停靠在岸边的船,从高高的船头上一跳,看谁最先摸到锚(现在想来真是危险。那锚可是几个尖锐的铁角啊)。也玩滑溜,先用水浇湿坡上的土,然后赤裸着身子,从高高的斜坡上滑到水里,溅起水花。有时候运气不好,硌到一片瓦子,顿时身上被划出一道血口。
务鱼。河里不少小鱼,斫根竹子,削去旁枝,用火薰黑竹节,就是钓竿。用蒜梗作标,抓包菜里的青虫,或苍蝇作饵,用钓竿连续拍水响以吸引鱼来吃,口里叫道:“钓竿蛮蛮长,钓了鱼的娘(钓大的)。钓竿蛮蛮短,钓个鱼的卵(钓不着)”。每天早上能钓个八九条,用竹笋、酸菜、辣椒一炒,那味,没得说。不仅自己能吃到鱼,而且还得大人们的赞许。用红瓜子作饵,在膝深的水里放下线钓,中午时分看一次,傍晚再看一次,往往能弄到一种半斤重的红眼睛鱼。那时候没禁止炸鱼。中午时间,看某个大人鬼鬼祟祟地揣个物体,在河边观望,我们估计他是要炸鱼了。我们就偷偷地跟在后面。等他一丢下炸弹,我们就纷纷跳出来,直扑水里,抢着捡鱼。水面上没鱼了,就沉到水底,睁开眼睛找鱼。有一次,大人刚丢下炸弹,还没炸,有个孩子就扑到水里了,炸弹一炸,震得他肚皮发麻。除了在河里务鱼,我们还在水塘里务鱼。花一上午或一整天,用脸盆把一个小水塘的水抚干,能抓到几斤鱼。
打土仗。一伙孩子为抢占一个高地,用土块做武器,迎面痛打。土块打着有痛,但不至于伤人。有谁遇上块硬点的,就痛得哇哇叫哭,战斗也就此停止。为躲避必然而来的大人的问罪,各自作鸟兽散。有一次,我们这村的孩子纠集一起,准备晚上攻击另一村的孩子,事先埋伏在路旁的一个甘蔗林里,摒住气等。突然,甘蔗林里的坟墓上站起一个白影子,大声喝道:“你们干什么?”我们被吓得魂不附体地跑。原来这老头是队里派去夜里照甘蔗的,是个鳏夫,他不怕鬼,鬼却怕他。夏夜里他直接就睡在坟墓上。
挖坑害人。在大人从地里劳动回来必经之路上,挖个深坑,放一堆牛屎,用树枝架上,盖上土,抚平,然后躲起来看。见人来了,既兴奋又害怕。突然,那人脚踩到了,踏入坑里,一脚牛屎,大骂不已,孩子们却大笑而逃。大人追,孩子逃,是那时常见的情景。有一次,一小孩挖好了一个坑,眼看着自己的父亲背个把犁过来,想喊又没敢喊。他父亲一脚踏进坑里,犁头刺背,闯大祸了。
务野食。谁家的桔子先熟,哪棵树的柚子好吃,哪家的枣子红了,我们摸得清楚。要偷哪家的吃,还事先与他家孩子通报,征得孩子的同意甚至支持:“今天晚上来偷你家的桔子,可不可以?”“不要,我爸爸今天晚上不会出去。”只好等明天了。
所有的板栗、甘蔗、西瓜都是公家的,有人守,可也是孩子们最喜欢吃的,怎么办?我们捡掉在地上的板栗吃,总可以吧?孩子们手持一根竹杆,说是扒草的,其实趁没人就挥杆打。衣服里揣着个尺把长的小木棍,趁没人,向树上一甩,哗啦就打落几球来。每个孩子一天都能“捡”到一两斤板栗,回到家,大人赞许得很。也有被抓到的。一般处理方法是缴了竹杆和木棍。有个外村的孩子被抓到了,生产队勒令他作检讨。孩子哆哆嗦嗦地念道:“今天,我爸爸买了肉,没板栗来煮,就要我来偷。我就来偷……我再也不来偷。”
偷甘蔗一般是晚上,夜里饿了,两个孩子互使眼神:“去吹笛么?”。偷甘蔗得有工具,到船厂捡来废锯条,磨成闪着寒光的匕首。趁没人,刺入甘蔗,旋转一下,倒了,一声没响。或向甘蔗林的一头里甩块石头,哗啦啦地响。守蔗人赶紧跑过去,喊“哪个在偷蔗吃?!”。这头,我们赶紧掐蔗,守蔗人想来抓也来不及了。
生产队特别看重对西瓜的防守。我们几乎难得手。有一次,我瞅见一个西瓜地只有两个老妈妈守,就约了个孩子去偷,结果被发现,我们慌忙丢了西瓜狂逃,没想到那老妈妈死心眼,硬是追了我们几里路。当我们越过另一个西瓜地时,被突然窜出的一个年轻人抓住了。任凭我们怎么辩解,他硬说我们是想偷他的西瓜。才刚刚摆脱老妈妈的穷追,又遭此黑天冤枉,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嚎啕大哭起来。年轻人这才心软,问我是哪家的。一问,原来与我家还有点亲戚。这才放了我们。后来我长大了,我再不认这亲戚了。
有一样非常平常但又美味的东西,小时候经常弄来吃,但长大以后再也没吃过,那就是柿子的籽。柿子青时,挖出它的籽,费很多工夫,把籽上的衣磨去,洗干净,又韧又软又甜。
夏日里,村里不时来卖梨瓜、卖冰棍的外乡人。梨瓜的浓香、冰棍的冰爽,让我们垂涎三尺。没有零花钱,怎么办?我们一是通过勤劳,去捡蓖麻籽、籽子、茶籽、挖半夏交到供销社去卖钱。也想办法去偷东西卖钱。造船厂需要使用大量的铁钉子,也使用各钟铁制工具。我们站在师傅旁边,“欣赏”他的工艺,他也洋洋自得地干得更欢。一不留神,我们就把他的工具或铁钉踢到一个脚落旮旯里,然后就走开了。等船厂下班了,我们急忙到旮旯里寻。多数时候是被师傅找着了,也偶尔没被找着,还在那里。我捡东西,又不是偷东西,不算犯法吧?于是心安理得地拿去卖钱了。一斤铁钉能卖两块钱,一个铁锤或一把斧头多少钱?孩子又不懂行情,“随你给吧”。
那时全村没有谁家出过大学生,读书考大学是连想都不会想的事。所以大人们虽然也重视孩子的读书,但抓得并不紧。考试吃多少分,只是一时地拷问,留级却是个面子上过不去的事。所以只要不老是留堂、不留级,孩子们是不学习当作回事的。剩下的事,还是玩。
终于,玩到头了。1981年,我十三岁那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大地上,无数的农村从此焕发生机,然而我的家乡却是开始苦难,对我则是快乐童年的结束。生产队解散了,船厂解散了,大队的制茶厂解散了,电灯没了,重新点煤油灯。家家户户为增加茶叶产量,支使孩子去采茶,我的轻松快乐的童年也随之结束。
采茶苦。一年有四到五季茶可采,分别是春茶、夏茶、秋茶和禾芽茶,每一季要采半个月以上。每一次都得采半个月以上,一大早就被叫起,采到上午九点才回家吃饭,饿得发慌。中午烈日当空,要到十二点才许回家。吃过中饭,孩子烧火,大人炒茶杀青。炒好了一锅,马上大人孩子每人一个茶团,趁热用手使劲揉,那个烫啊。手上、脸上、身上全是汗水,洒入茶团里。揉完茶,晾晒,已是中午两点。休息一下,马上又得顶着烈日去翻转茶叶。下午三点,还是骄阳似火,就得出门了,一直要采到天黑伸手不见不指,才回去。因为怕误了茶时,也误了其他许多农活,所以非得赶紧把茶采完。晴天采,雨天戴着斗笠也得去茶。半个月下来,手指都采得开裂,贴上胶布还得继续采。茶树上有一种虫,十分毒,一碰着它就会刺得疼痛难忍。日复一日地重复,让人心烦不已。
与此同时,茶农的命运也走下坡路了。国家取消“返销粮”,茶农要到自由市场上买黑市粮吃。每斤四五毛,一直涨到八毛九毛,而此时的茶价却贱如狗屎,每斤三四元。为维持生活,茶农只得增加产量,孩子们稚嫩的肩头上担子也加重了。
为赚生活,只13岁的我,参与到一切超强劳动中,运粪、劈草、斫茅、锄地、扶蔗基(夏日里在密密的甘蔗林中,穿着厚厚的衣服劳动,一呆就是几小时)、砍甘蔗、削甘蔗、背甘蔗。然而,即便如此,还是没能改变越来越穷困的面貌。为供养我在县城读书(全家唯一能突围出去的希望),几个兄弟不得不辍学回家。我祖母逝世,父母亲无力办丧,只得变卖母亲陪嫁的首饰。整整一称盘的银链加戒指加耳环,只卖了六十元。
生活越来越愁苦。为供养我读书,家里不得已而经常举债。每次回家要钱,当看到父亲去向人借钱时,我心如刀绞。在这节骨眼上,我的一个辍学在家的哥哥由于悲观而弃世,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生活艰难。悲痛使母亲此后经常以泪洗面,几年后她也作了同样的选择。
我的母亲,我可怜的母亲。
再见,我的快乐童年。
| 初级会计职称 | 指南 | 动态 | 查分 | 试题 | 复习 | 资产评估师 | 指南 | 动态 | 大纲 | 试题 | 复习 |
| 中级会计职称 | 指南 | 动态 | 查分 | 试题 | 复习 | 高级会计师 | 指南 | 动态 | 试题 | 评审 | 复习 |
| 注册会计师 | 指南 | 动态 | 查分 | 试题 | 复习 | 会计基础知识 | 指南 | 动态 | 政策 | 试题 | 复习 |
| 税务师 | 指南 | 动态 | 查分 | 大纲 | 复习 | ACCA考试 | 指南 | 动态 | 政策 | 试题 | 复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