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实行“费改税”不符合中国国情
最近一段时间,社会保障改革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焦点话题,有学者主张我国应推出规范、稳定、低运行成本的社会保障税,争取实现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部分)的“费改税”,并建议将社保基金纳入公共财政框架之下。就这一热点话题,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所长郑秉文。
记者: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出现了每年超过20%的可喜增长,最近学术界有这样一种声音,认为应该尽快实现社会保障费改税,用国家财政为依托,解决多年以来难以解决的社会保障制度难题,对此您是怎样看的?
郑秉文:您提的这个问题涉及到与国家财政之间的关系。任何一国社保制度,既与其财政有关系,又没有关系。所谓有关系,是指基本社保的举办人是国家,是强制性的,在世界各国实践中,当社保制度出现赤字时,所有国家都出面进行转移支付,予以补贴。所谓没关系,是指任何一国政府都追求社保制度收支的基本平衡,并且将之作为一个制度目标,由于老龄化等外部原因,社保收支出现了不平衡,财政负担吃不消,于是才出现了风起云涌的世界范围内社保制度的改革浪潮。任何一国基本养老制度的融资都首先是由雇主和雇员双方供款构成的,这是制度的主要收入,追求制度的收支平衡,减少财政负担,这是政府设计社保制度时的一个制度目标。所以,世界各国不管是实行缴费制还是缴税制,例如,英美是缴税制,德法是缴费制,但他们都是算经济账的,都是追求制度本身收支平衡的。说到这,顺便提一句,近来学界有人提到借鉴德国的“自治型”模式,意思是说,要加强个人缴费与未来待遇之间的联系,尽量追求制度收支平衡,而不是说采取行业统筹的方式,那就成了制度的碎片化了,这不是我国设计的制度目标。追求制度收支平衡,与自治型和政府主导型也没有关系,我们国家的社保制度当然应该是政府主导,这是毫无疑问的,是十分正确的,行业统筹的自治型制度是一百多年前欧洲等国家初建社保的制度雏形,是历史为欧洲一些国家留下的遗产,在现代社保制度里,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走这条老路。话说回来,经济高速发展,财政收入高速增长,不是放弃追求社保制度收支平衡的理由,而只是为政府提供财政补贴提供了方便而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由于经济实力雄厚,比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就与财政混合吃起大锅饭,甚至将之成为社保制度追求的目标。所谓以国家财政为依托,对目前我国来说,首先应该是指解决转型成本,然后是指对当期缺口的转移支付。
记者:您认为费改税将对我国目前实行的统账结合养老保险模式产生怎样的影响?在财政乐观下,企业养老保险能否推广到全民?国家财政能否解决社会统筹难题,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郑秉文:是采取缴税制还是缴费制,与是否以普享型社保制度为制度目标有关,还与具体社保制度结构有关。一般来说,普享型社保制度采取缴税制,因此,未来待遇与个人社保供款的多寡关系不大,社保制度基本覆盖了大部分就业人口;但是,覆盖面非常小就不可能建立一个普享型的制度,比如我国目前只覆盖就业人口的不到20%,甚至就连城镇的非正规部门即灵活就业人员还没有覆盖进来,“小三农”(农民工、失地农民和务农农民)更是遥遥无期,在这种条件下,采取缴费制可强化个人缴费的激励作用,防止道德风险,有利于激发社会成员参保的积极性,有利于扩大覆盖面。目前的最大国情是二元经济,统筹层次太低,主要是以县级为主,这在全世界也是少有的和不公平的,这种“地方粮票”严重地影响了全国范围劳动力的流动和全国劳动力市场形成,如果采取缴税制,杀富济贫的效应就会降低发达地区上缴社保供款的积极性,道德风险导致统筹层次难以提高,就是说,在地区之间也存在道德风险问题。最后,我国实行的是统账结合制,其中个人账户供款带有强烈的个人储蓄性质,明显的返还性质,与税收性质正好相反,如果费改税,就与制度结构产生严重冲突。上述三个理由说明,费改税存在很多问题,对个人账户供款来说是不公平的,对实现广覆盖是不利的,对提高统筹层次也是不利的,而这些,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实行费改税就正好背道而驰。财政状况的好坏与实现广覆盖和提高统筹层次是没有关系的,而关键在于社保制度本身的设计是否符合国情。
记者: 这一讨论涉及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看我国当前的基本国情以及到底我们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保障,以社保基金为支撑的社会保险,与以财政为支撑的社会保障,在当前的情况下,哪一个更有利于实现全国的公平的公正的广覆盖?您认为我国当前社会保障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郑秉文:外部条件是二元经济,内部条件是统账结合,这是最基本的国情。是否实行费改税,主要取决于这两个基本国情。尽快提高统筹层次以实行“全国粮票”,扩大覆盖面以实现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保体系,这就是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切制度设计都应该服从于这两个目标,这是最大的任务。恰恰相反,实行费改税既不符合上述两个基本国情,也不利于实现上述两个最大任务。至于建立一个是以社保基金为依托还是以财政为依托的社保制度,如前所述,我们应顺应历史潮流,建立一个以社保基金为依托的制度,这是社保制度的“本”,国家财政只应承担起最后担保人的作用。这个问题实际涉及到最近发生的一个争议,即社保资金管理形式是“单独预算”还是公共财政下的“联合预算”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单独预算是个假命题,认为一个政权体系只应有一套预算,担心单独预算会导致部门权力膨胀,社保部门会成为“第二财政部”。
这个观点和担心是客观存在的,但问题比较复杂,它涉及到社保资金投资策略的选择问题。在统账结合制度下,账户基金投资策略假定主要以市场化投资为主,这里说的主要是统筹资金,并假定统筹基金的投资策略只有国债投资和股市投资两种形式,这时,采取什么管理方式对中央预算就会产生短期和长期两种不同的影响。先看“短期影响”:在单独预算下如采取股票投资,就可将之不列入中央预算支出,对其是否平衡就不会产生影响;但在联合预算里,则会显示为盈余减少和赤字增加,并在账面上表现为政府总储备金的减少(因为投资股票而减少了投资国债),这样,就需要等量的公共借贷;如果出现投资盈余,就有可能将政府其他项目的真实财政状况“隐藏”起来并显现在账面上,而潜在收益则需若干年以后才能显现,于是就会出现当期成本与收益之间的“不一致性”,使政府和公众很难对财政状况和股票投资进行评估。但对资本市场总量来说,投资股票的“账面赤字”将不会有多大影响:一方面中央财政的公共借贷可吸纳资本市场的资金,而另一方面投资股市却可抵消这部分流出,同时,私人投资的年度基金总量变化不大。再看“长期影响”:不管采取单独预算还是联合预算,任何投资策略对中央预算的影响均主要呈中性:如果股票投资收益超过公共借贷的成本,中央预算不会受到较大影响,国民收入也不会出现明显的增加,这时只是获得了原本属于私人投资者的一部分股票收益;如果投资收益正好等于政府公共借贷,就很可能产生利率上调的压力,这时对股票的再投资和政府发行债券就会产生一定负面的影响。
在世界各国的实践中,有的采取单独预算,有的是联合预算。有些国家经历了一些曲折发展过程,例如,美国1935年建立社保制度时采取的是单独预算,没有列入联邦预算,1967年改为联合预算至今。学界对此始终存在较大争议,许多经济学家主张将之从一般预算中独立出来,认为联合预算存在许多弊端,例如夏文教授(J.B.Shoven)2003年指出,美国社保资金“购买特殊联邦国债以后财政部将之用于政府的其他支出……一旦这笔资金转移至联邦基金就与诸如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与其他公共借贷混淆起来,这笔资金的用途就再也无从追踪”。
从世界各国发展的趋势上看,为追求社保基金收支平衡,减少财政负担,社保基金采取独立于财政性资金的单独预算管理是个好办法。对我国来说,它可起到鼓励缴费和扩大覆盖面的激励作用,就目前阶段来说,覆盖面太小是最大的不公平,扩大覆盖面,尽量实现应保尽保,让更多的人享受社会保护是最大的公平。担心社保部门会成为第二财政部,这种担心在法制国家是多余的,因为理论上讲,社保部门只是一个执行机构而已,社保资金的收支与使用是经过授权的,甚至最终是经过立法部门通过的,即使在单独预算条件下也是这样。
记者: 您认为在未来的社会保障改革中政府应该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发挥一种什么样的作用?
郑秉文:在中国社保制度建设中,中央政府毫无疑问应当承担起主导作用,否则,一切将无从谈起。而目前的倾向是中央权威逐渐表现出软弱的倾向,尤其在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的博弈之中,遇到责任就推诿,遇到利益就争抢,中央政府没有发挥强有力的裁决作用。这里要澄清一个误区,即有学者将政府责任与纳入预算混为一谈。是否采取单独预算是一回事,是否将其纳入预算是另一回事。从战后初期至今的半个多世纪里,欧洲一些国家经历了一个逐渐将其纳入预算的过程。德国是1965年正式纳入联邦预算的,法国是1996年规定由国民议会对社会保障预算进行年度审查,2000年正式纳入预算的。即使正式纳入预算,国民议会对社会保障收支几乎也没什么实质监控权,议会的作用微乎其微:第一,法国社保费(法国称之为“社会分摊金”)不需要议会批准,不受年度总预算原则条条框框的制约。第二,法国社保费的收支平衡等均由每个行业基金自负其责,具体事宜由具体法令或社会伙伴签订的协约来确定。第三,由于国民议会“监督”作用一直停留在“听取汇报”的阶段,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预算,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决算可言。
当然,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是逐渐将之纳入预算范畴,这是战后半个世纪以来的总趋势,但这不等于实行联合预算账户。对中国来说,目前中央政府承担的责任不在于是否将之统一纳入中央预算盘子,这是表面文章,甚至,就连费改税的争论都是表面文章,这是典型的避重就轻,在细枝末叶上纠缠不休的表现,而另一方面,重大的制度设计问题却无人问津。当前最急迫的是,政府应积极解决社保制度基本框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制定一个可以覆盖到全民的、全国统一的总设计方案。在这些重要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过多地争论是否进行费改税,纠缠在枝节问题上,不仅有些早,而且还有部门利益之嫌。政府的责任和作用,应该是从战略的高度来看待现在争论的一些技术问题,从全社会的长期利益处理一些枝节问题,从有利于社保制度长期建设的角度来起草《社会保险法》,就是说,政府最大的责任和最大作用就是不遗余力地推动社保制度建设,否则单就技术谈技术,就分散了社保制度长期设计的精力,撂荒了国民百姓的根本利益。
上一篇:毛建国:油烟熏出来的纳税百强


 新用户扫码下载
新用户扫码下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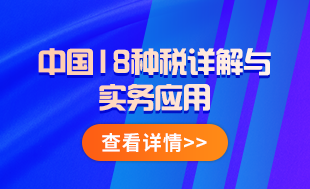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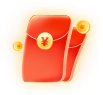

 新用户扫码下载
新用户扫码下载

